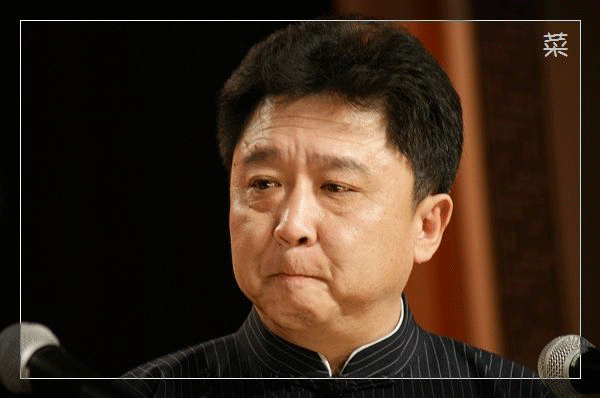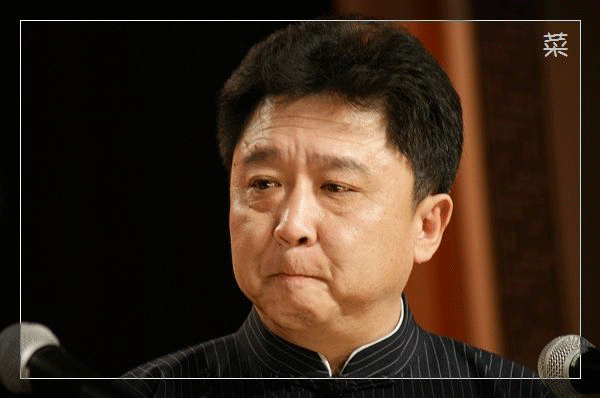文|北方女王
3月22日,电影《老师·好》如期上映,于谦不说相声了,当了一回班主任,尽显80年代的校园百态及师生情。
镜头下的他,脱下大褂,穿上白色衬衣,戴上了黑框眼镜,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,漫步于校园林荫小道,开始“误人子弟”,
电影末了,班主任苗宛秋说:“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,而是遇见了你们,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。”

这个头戴“相声皇后”美誉的于大爷,截止今日,参演过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超过58亿了。
许多观众流着眼泪离开影院后,不禁发出感慨:大爷不老,我们都欠他一座影帝奖杯!
当曾经的摇滚老炮儿们纷纷拿起保温杯泡上枸杞,于谦反而穿上牛仔衣,头顶新卷发,踱步上台吼起了崔健的《一块红布》。
各位您瞧见了,这才是京城顽主该有的样子。

问:于谦他爹是谁?
答:王老爷子!八大胡同董事长!
问:于谦他儿子是谁?
答:郭小宝!
问:于谦三大爱好?
答:抽烟喝酒烫头!
人生五十余载,于谦却始终活得像个“玩世不恭”的孩子,游离于自己的一方土地,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。
人在江湖,远离喧嚣。
自得其乐,逍遥处世。


关于“玩”的心思,于谦可谓是天性使然。
他的父亲是大港油田地质勘探老总,副局级干部;母亲也是石油炼厂方面的专家,家境颇为优渥。
混迹于北京大院儿的于谦,是个地地道道的“京城少爷”,从小跟姥姥和5个姨妈长大。
“你想想,这样的组合得对我纵容到什么份儿上”。

他自小便养成了爱玩儿的脾性,上小学一年级时,路过官园花鸟鱼虫市场,手里紧紧攥着五毛零花钱,野心勃勃买了两只粉眼鸟,如获至宝,抱着屁颠屁颠回家了。
那可真是提笼架鸟,飞鹰走狗,打鱼摸虾,豁豁庄稼,老北京八旗子弟玩啥他玩啥。
爸妈为之担忧,他反而觉得:
“哪能天天忙正事,一根弦绷得那么紧,干嘛呢?”
院儿里的邻居看到他都说:“这孩子,真是个少爷秧子。”

十二岁那年,刚上初中的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,退学去了曲艺团。
可老师觉总得他不是这块料,瞧这“死羊眼,一张脸”,眼睛、表情都不灵动,不适合相声表演,劝父母“赶紧带孩子走,别耽误了孩子”。
那时的于谦,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他跟着一位学长苦练了一周,等到验收那天,团长、书记,还有在学校执教的相声名家王世臣老先生都坐在台下。
他刚讲了一小段,王世臣扭头就问:“我看这孩子不错啊,留下吧。”
于谦顺理成章留了下来,为了心中所爱,他寒冬腊月,天不亮就起床到团里,集体坐卡车到农村演出,一天演三场。
将两个拖拉机倒着开,两斗碰上以后,槽帮一卸,便是舞台。两个屏光一打,开演!
演出结束,身子也冻透了。
他每场演出拿到的酬劳只有几块钱,条件异常艰苦,却乐在其中。
险些被劝退的经历和演出环境的艰苦,都没有给年少的于谦带来任何烦恼,相反,在他眼中只有集体生活的无忧无虑。
毕竟在于谦心中,生命中一定要有所热爱,方可玩得有底气。


可生不逢时,于谦从学员班毕业一年多以后,相声淡出主流娱乐,演出越来越少。前路十分渺茫,他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。
彼时的相声几乎淡出了老百姓的视线,演出没人邀,走穴没人用,慰问没人听,晚会没人看,上班没人管,排练没人理,单位没人情,领导没人味儿。
1994年,正值流行音乐、霹雳舞、魔术风靡之时,于谦每每都是硬着头皮上台演出,思虑着“我要跟他们说点什么,才能不往下哄我呢。”

面对观众哄台,于谦开始表演吉他相声,在旁人看来无法忍受的委屈,他却视为乐趣所在。
于谦热爱相声,靠其谋生,却遭遇无处可说的境地。
名义上能挣400多块钱工资,实际上扣除各种罚款,工资到最后就剩一块两毛。
曲艺团没落之时,于谦刚娶了媳妇,心里这叫一个急啊。只要回到家,就会听到媳妇问“咱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啊?”
眼看相声没落饭碗难保,他摸了摸干瘪的钱包,意识到“玩不起了”,为了生存,他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大专班,进修了两年。
随即开始演小品、话剧、拍电影、电视剧、接广告、当主持人,什么活儿都能玩出名堂。
这个世界之所以乏味不堪,有时就是因为功利的聪明人太多,有趣好玩的人太少。

有趣不是沽名钓誉的与世为敌,有趣是如日中天时仍敢遗世独立。
他在自传《玩儿》这本书中,记录了第一次接到剧组邀请时的心情:
当晚回到家,我也碰上了难得一遇的好事儿。一个哥们打来电话,说剧组急招演员,他推荐了我,要即刻动身,越快越好,到苏州拍戏一个月。这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馅饼了!
跑了十几年的龙套,他从不懈怠,无数的配角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。
在电视荧幕中,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于谦: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中的街头警察,《京华烟云》里的管家,《北平往事》里的伦德昌,《笑笑茶楼》里的冒牌经理......

就算是出场戏不足三分钟的路人甲,他也用尽全力在这些角色上放入不同的性格。
融入到市井百姓里,演出他们的不同样貌。
别人吃不了的苦头,在他看来不过是另一种玩法。生活远远不止一种方式,只要认真便可寻到意义,活出自我。
真正有趣的灵魂,不仅仅在于生活一帆风顺时,能把柴米油盐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更在于历经千帆后,敢于直面生活的惨淡,把一地鸡毛的琐碎变成一句风轻云淡的笑谈,挥一挥衣袖。


直到于谦28岁那年,他碰到了日后人生重要的伙伴郭德纲,埋藏于他内心的相声梦再次被点燃。
两人见面的第一句话,郭德纲问:“以前学过?”
于谦回答:“学过,有日子没说了。”
来上几场相声后,两人互相感觉特别好,默契日渐趋同。

郭德纲对他说:“哥我这有个小摊子,叫北京相声大会(德云社),没多少人,也不挣钱,就为玩,你什么时候到我这看看呢?”
德云社创立初期,几乎入不敷出,步履维艰,于谦却毫不犹豫,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。
两人一路走来,珠联璧合,在舞台上他反应非常敏捷,甘愿做郭德纲身边的绿叶,善于捧哏。
“我说相声不是为了出名,而是爱相声。”
十年时间里,吃尽苦头的两人终于火了。火到在保利剧院创造了返场22次的奇迹,成了中国相声的一面旗帜。
这对搭档,随之红遍大江南北。

在相声舞台上,他自在、从容、快乐。有他的地方,总是笑声不断。
郭德纲的很多包袱,都是靠于谦的捧而爆笑全场。
因常被郭德纲戏虐,以至于网络上有“德云社的票房有一半是靠于谦老师的父亲撑起来的”这种说法。
2013年,于谦把手机里积攒的十几万字集结成书,取名《玩儿》,作为多年搭档,郭德纲给自己的“皇后”亲自写了序言:
和于谦师哥相识十余载,合作极其愉快。台上水乳交融,台下互敬互重。抛开专业,谦哥在“玩”之一字上堪称大家……
接触十几年了,我对谦哥甚为了解。他不争名,不夺利,好开玩笑,好交朋友。在他心中,玩儿比天大!
在大多数人眼中,于谦只是郭德纲身边的绿叶。郭德纲却说:他活得比我值!

多年来,德云社风起云涌,几度被推上风口浪尖,于谦身处风暴中心,却岿然不动,抽烟喝酒烫头,总能云淡风轻地置身事外,以低调内敛的形象示人。
争来争去说到底不外名利两个字,恰好这两字,在他看来是最无用的。
所谓的爱玩背后,又何尝不是一份世风日下的淡泊明志。
人生苦短,倏忽而逝。知天命的年纪,于谦早已活得明白,也看得透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