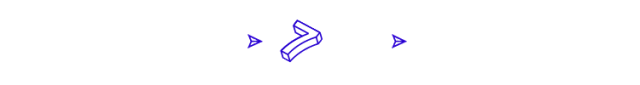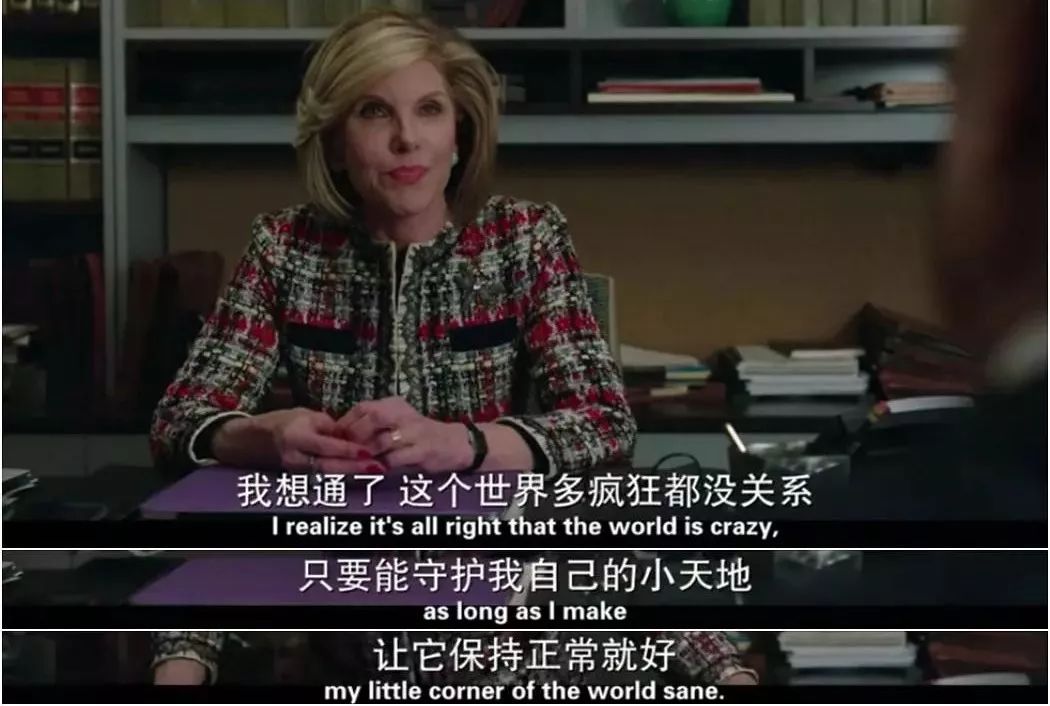from《The Good Fight》
我的好朋友孔轶群(化名)失业了,在2019春节假期前的一个礼拜。那天,他刚刚修改完晚间准备发送在公司微信公众号上的文案,在还有5分钟就能打卡下班时,他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:
“你的状态有很大问题,可能已经跟不上公司发展的节奏了,你走吧”。老板面带微笑地说完这句话后,递给他一份准备好的离职申请,只等孔轶群签名。
那一刻,孔轶群觉得自己像头老驴,刚从磨上下来就要被做成驴肉火烧那种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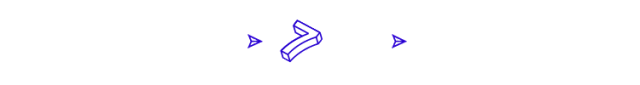
2018年对于不少人来说,是灾年。如果上半年媒体热炒的“消费降级”是某种灾难的前兆,那下半年随之而来的裁员潮则让很多90后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“凛冬已至”。
孔轶群在凛冬中,被冻得够呛。
孔轶群2017年大学毕业,毕业后就来北京工作了。说起他的学校名字,在南部省份中也算是响当当,只是他的专业名字看上去十分无关紧要也不被社会需要。这导致他后来从事的工作,和本专业没有任何关系。仗着文字能力还不错,他来到北京后,当了一名光荣的公众号编辑,成了我的同行。
在这一点上,我和他十分相似。唯一不同的是,我偶尔可以在东七门写自己喜欢的稿件,不太用经常鸟别人。而他,在一家乙方公司,公司旗下公众号几乎都是为客户爸爸服务的。
客户是公司的爸爸,公司是一个大家庭,老板当然是家长。于是从逻辑上来说,孔轶群等基层工作人员的地位,大致可以用“孙子”二字来概括。

from《The Good Fight》
不过,通过一定程度的心理建设,“装孙子”也可以是一件好事。就拿在北上广深等等一线城市的打工仔们来说,当大家亲身体验到恐怖的早晚交通高峰、林立的高楼、汹涌的人潮、昂贵狭小的出租屋再加过几次莫名奇妙的班后,多数会产生两种感情:
第一种:“哇我真的好渺小啊!这城市这么大可是什么都不属于我,我努力的意义是什么呢?唉生活真难!”
第二种:“哇我真的好渺小啊!这城市这么大可是什么都不属于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在这里,我真牛逼!”
孔轶群毫无疑问属于第二种,虽然嘴上不承认,但是对于千千万万和孔轶群一样的打工仔来说,北京是一片追梦之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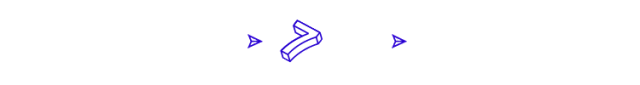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在公司内部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孙子,但是孙子有孙子的好,孙子可以得到“宠爱”。得宠的孙子,总会产生自己是一家之主的错觉。
就拿孔轶群来说,他工作的地方在北京朝阳区望京地区某高层写字楼内,属于初创公司。几个合伙人岁数都不大,有的有留学背景,有的曾在BAT里面的B做过事儿。公司的招聘页面上写着公司的优势:
“美女如云”、“弹性工作时间”、“零食水果下午茶无限供应”、“领导nice”、“前景好”、“不打卡”、“扁平管理”等等。

from《The Good Fight》
孔轶群刚刚入职的那段时间,感到十分幸福。同事都是年轻人,相处起来非常融洽;领导也没领导的架子,毕竟整个公司也只有30个人左右;零食水果无限量供应是真的,老板偶尔还会订一堆外卖请客。
他尤其喜欢和同事们开会时的氛围,一个又一个的创意方案在类似吵架拌嘴的会议上迸发而出,给了孔轶群极大的成就感。
虽然孔轶群的工资即使是在同行业里,也算不上高,扣除了房租之后,也不剩下啥了。不过这并不能让孔轶群心中奋斗的小火苗熄灭。
直到去年夏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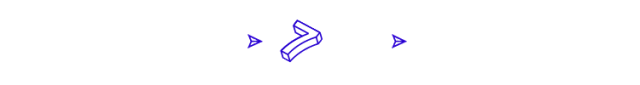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问孔轶群他自己觉得为什么被老板裁掉时。他说自己也不太清楚,可能是因为一篇广告的文案,他和负责内容的老板争执了很久。而且,在那次争执之后的第三天,他就被签了离职申请书。
不过,我并不这么认为。
去年秋天,孔轶群被诊断出来重度焦虑症以及轻度抑郁症。而之前的一整个夏天,他都在疯狂的加班。
在他的公司,加班是常态,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老板和员工之间存在时间差:老板在上午从来都不会出现在公司,但是员工一上午不出现是断然不可以的。这导致了所有需要老板参与的会议、定夺的内容从时间上都要往后推一到两个小时。
这也意味着,从正常点7点下班,变到晚上9点。
不巧的是,孔轶群同组的一名同事在6月份离职了,而老板似乎没有新招人的打算。原来两个人可以分摊的活,全部落在了孔轶群的头上。公司接的项目也没有变少,孔轶群的加班时间从9点钟跨越到凌晨12点,甚至有好几次直接干到凌晨4、5点钟。
加班费是肯定没有的,毕竟人家在招聘时写得明明白白:“弹性工作时间”。
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,让孔轶群的神经始终高度紧绷,休息严重不足。面对客户的要求、老板的看似慰问的责难,他也只能全部吞下去,然后转化成生产力。

from《The Good Fight》
当他发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(失眠、焦虑、注意力无法集中、双手发抖)之时,秋姑娘已经给北京披上的金色的外衣。在秋天这个分手的季节,他收获了焦虑症、0元加班费、因工作太忙离他而去的女朋友以及一分钱都没涨的工资。
原因不必再详述,总之经历了这些的孔轶群决定:从此不加班。当然,也是新来的同事帮他分担工作才让他有了底气。
从此,他每天按时上班,也按时下班。只要将手头的工作完成,他就极少在公司逗留。至于后续的沟通修改工作,要么在家要么在路上,总之永远不再公司等着。
不过,按照公司规定10点-7点正常上下班的他,也成了公司的异类。他渐渐地感觉到,自己被区别对待了。
其中,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。是中午吃完午饭后,大家都趴在工位上休息。半睡不睡的他被老板“啪啪啪”三声拍桌子惊醒了。
“别睡了别睡了,睡够了吧?轶群,我觉得你最近的状态很有问题,找时间我们聊聊吧!”
后来的事儿,大家就都知道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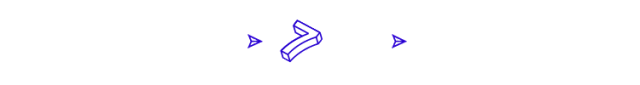
被开之后,公司补偿了孔轶群一个月的工资。
我觉得公司做的十分良心,因为从法律上来说,孔轶群签的是主动离职申请书,公司完全可以一毛钱不给。
过年回家他没敢告诉家长自己被开除的消息,和家里的亲戚吃饭时。亲戚都夸他:“好小子,在北京上班,将来肯定有出息。”
孔轶群就埋头吃饭,不说话。年后又回了北京,没办法,票在被裁员之前就已经买好了。
他也没急着找工作,反而去大理玩了一段时间。住青旅,认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:休年假的白领、四处旅行的纹身师、深藏不漏的吉他高手等等等等。
在洱海旁的酒吧里,一瓶一瓶地开着高于市场价的啤酒。孔轶群第一次感受到了诗和远方的魅力,曾经的社畜生活在现在看来,如此的可笑。
不过,孔轶群很快就笑不出来了,因为钱花的差不多了。
上周末,他刚从大理回北京,无差别乱投了若干家公司的简历,他想去的都没给回复,邀请面试的都是他看不上的。
当然,更多的是石沉大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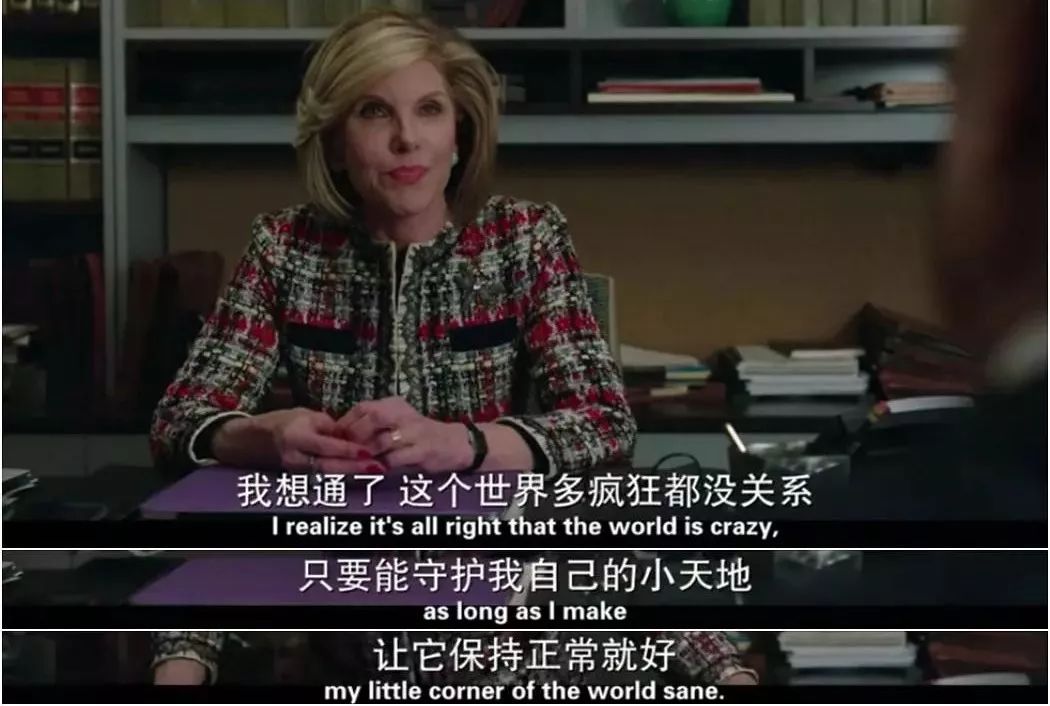
from《The Good Fight》
他回来之后,我俩见了一面。我安慰他说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