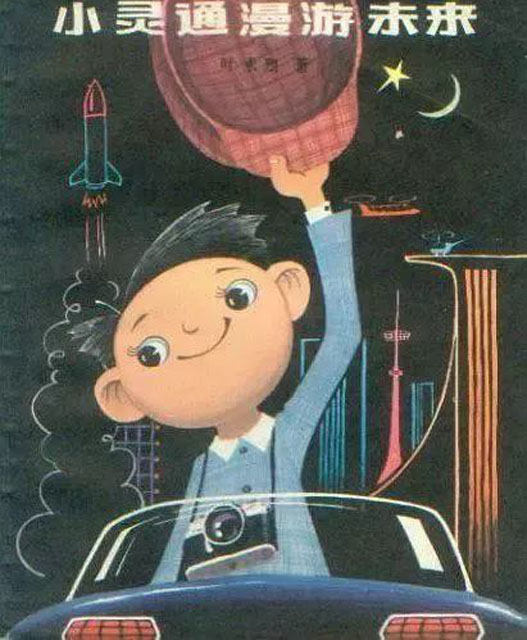善良的科学,跟万恶的鸦片一起手牵手进入中国。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,跟坚船利炮一起来华的外国传教士,给只知道科举八股的中国人带来了牛顿和笛卡尔,中国的第一次科普热潮由此而生。半个世纪后,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了美国作家爱德华·贝拉米的小说《回头看纪略》,1891年开始在《万国公报》上连载,因此这一年是科幻小说引进中国的元年。
翻译之后是原创。慈禧老佛爷七十大寿的1904年,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《月球殖民地小说》开始连载,作者署名荒江钓叟。早在此前一年,日本留学生周树人同学就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自己从日文译本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·凡尔纳的名作《月界旅行》和《地底旅行》,对未来充满好奇的同时,对自己的民族抱有莫大希望,“冥冥黄族,可以兴矣”。
再过十五年才会诞生的鲁迅,那时当然正在做梦,但做梦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。晚清的科幻小说风行一时,许多都带有传统文化的痕迹,例如作家吴趼人的《新石头记》,就写贾宝玉经过几世几劫,重新来到一个科技昌明的文明世界,甚至坐上了潜水艇。

然而奇怪的是,五四运动后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正式进入中国,科幻小说却反而突然偃旗息鼓了,取而代之一批以现实主义挂帅的作品。鲁迅这时正忙着写阿Q调戏小尼姑,再也没有闲情逸致搞什么科幻。据学者王德威推测,也许是因为当时军阀林立、内外交困、国难当头,实在是缺少时间和精力来幻想一个现实之外的科学空间。
因此民国时期,更多是以科幻小说的筐来装现实的内容。沈从文模仿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,写《阿丽思中国游记》,对当时的时局乱象极尽嘲讽;老舍写《猫城记》,写一个太空人因为飞船失事来到猫国,猫国人虽然大难将至却天天内斗不休。与其说他们写的是科幻,不如是借科幻之名、行针砭之实。毕竟,谁也没有期望典型的文科生老舍和沈从文,会真的有多少科学知识。
2
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,苏联给中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,科幻也不例外。实际上,“科学幻想小说”一词即从俄文翻译而来。此时的科幻小说被归在科普创作和儿童文学之下,受众只有一种:小盆友。
1954年,25岁的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生郑文光写了《从地球到火星》,成为1949年之后第一篇人物和情节俱全的科幻小说。虽然只是短篇、情节也不复杂,但竟然引起了北京地区火星观测的热潮,跟今天的父母带孩子逛科技馆一样,人们排着队去建国门的古观象台看星象。中国的科幻小说,终于姗姗来迟地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潮。
1959年暑假,19岁的北大化学系学生叶永烈,开始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写科学小品。两年后,五本一套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首次出版发行,成了之后四十年里几乎无人不知的科普畅销书,而叶永烈是主要作者中最年轻的。同年,叶永烈完成了他的科幻小说处女作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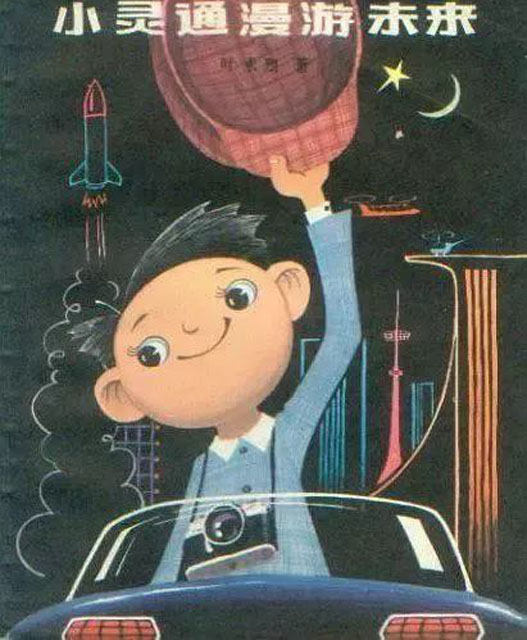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,一批科幻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。1960年,25岁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童恩正发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说《五万年以前的客人》,而且也已经写成了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初稿;1962年,成都地质学院的教师刘兴诗发表了《北方的云》。
但好景不长,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,让科幻小说作家噤若寒蝉。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下,科幻小说没有容身之所。例如刘兴诗因为六篇科幻小说而吃尽苦头,一度发誓今后再不写任何文章。
3
冬天过后是春天。1976年,叶永烈发表了1966年之后的第一篇科幻小说《石油蛋白》,标志着科幻小说的复苏。两年后,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,开幕式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作重要讲话,中国迎来了“科学的春天”。年底,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,科幻小说也随之一路向上。
也是在这一年,叶永烈写于十八年前的处女作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正式出版,首印150万册、前后发行300万册,当时的天文数字纪录迄今也难打破。同年,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正式出版,两年后更被拍摄为同名电影,也是国人平生接触到的第一部国产科幻电影。

此时的科幻作家,已经不满足于科普和儿童文学的定位。1979年1月20日,童恩正发表《幻想是极其可贵的》,明确提出科幻小说的文学性重于科学性、科幻小说应从传统的科普工具模式中解放出来,发挥更大的意义。
同年年底,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·阿尔迪斯访华,参与交流的中国科普作家满怀期待地询问他“英国科幻小说怎样教育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?”结果阿尔迪斯的回答把在座的中国作家惊呆了。
他说,科幻小说没有科普的义务。科幻小说的立足点是现实社会,是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。科幻小说是文学,科学只是外衣。科幻小说的目的不是传播科学知识。
阿尔迪斯跟童恩正如出一辙的观点,既给了中国科幻作家以启迪,也悄悄地在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,奏响了冬天的曲调。
4
科幻小说目的不为科普,这是科学家难以接受的。对科幻小说的攻击,首先便来自部分著名的科学家,例如德高望重的钱学森。
1980年,堪称当时中国最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表示,“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,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。”他坚决反对科幻小说不归“科学”归“文学”,用现在的话讲,就是一切不以科普为目的的科幻小说都是耍流氓。
科幻小说作家对此当然是不以为然的,例如杜渐就分辨:
“科学小说不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,一如历史小说不是宣讲历史知识的教科书、武侠小说不是传播武功的秘籍、战争小说也不讲授作战的军事常识一样。假如反过来说,科学小说必须传播科学知识,那么爱情小说岂不要教人恋爱方法,成了‘爱情大全’了吗?”
虽然各有理由,但话语权是有相当差别的。钱学森的相关批评可以被刊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杜渐当然难以相提并论。而到了1983年,对“科幻小说”的批评,渐渐与“清除精神污染”合流。而批评的基调,也逐渐严重起来。
例如钱钟书的堂弟、中科院院士钱钟韩就针对科幻电影《星球大战》表示,“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。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、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……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,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。”这名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的研究生,观点当然有相当的说服力。